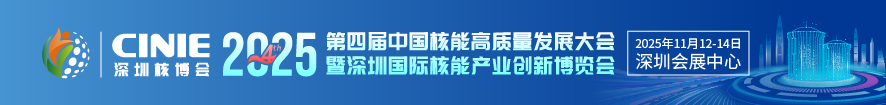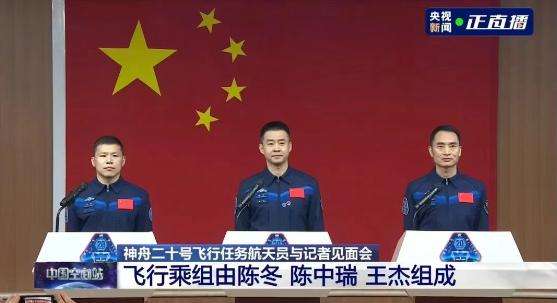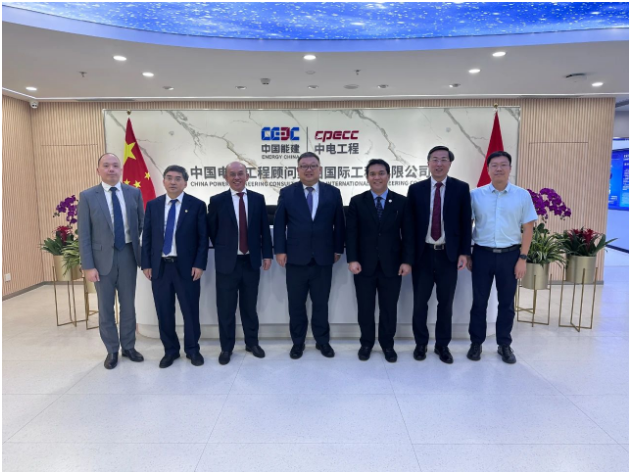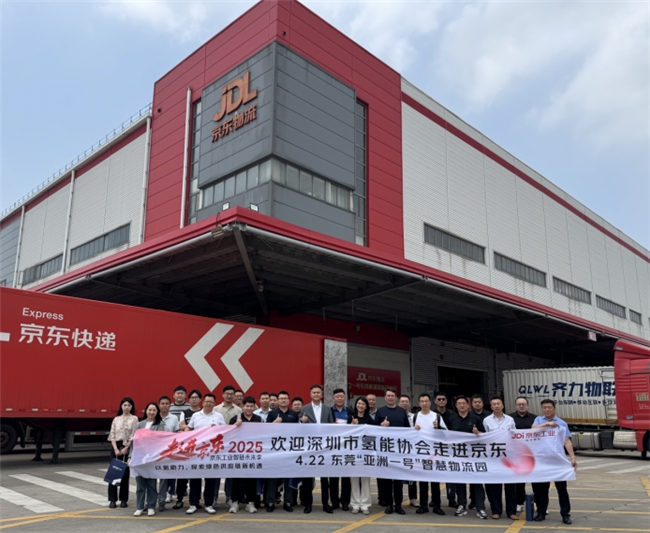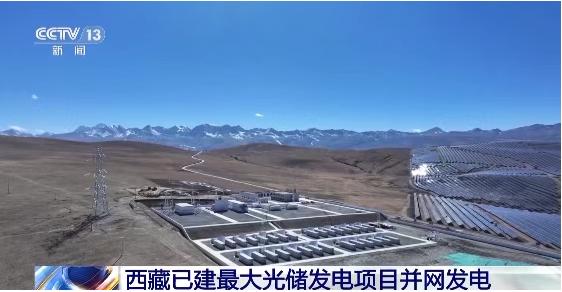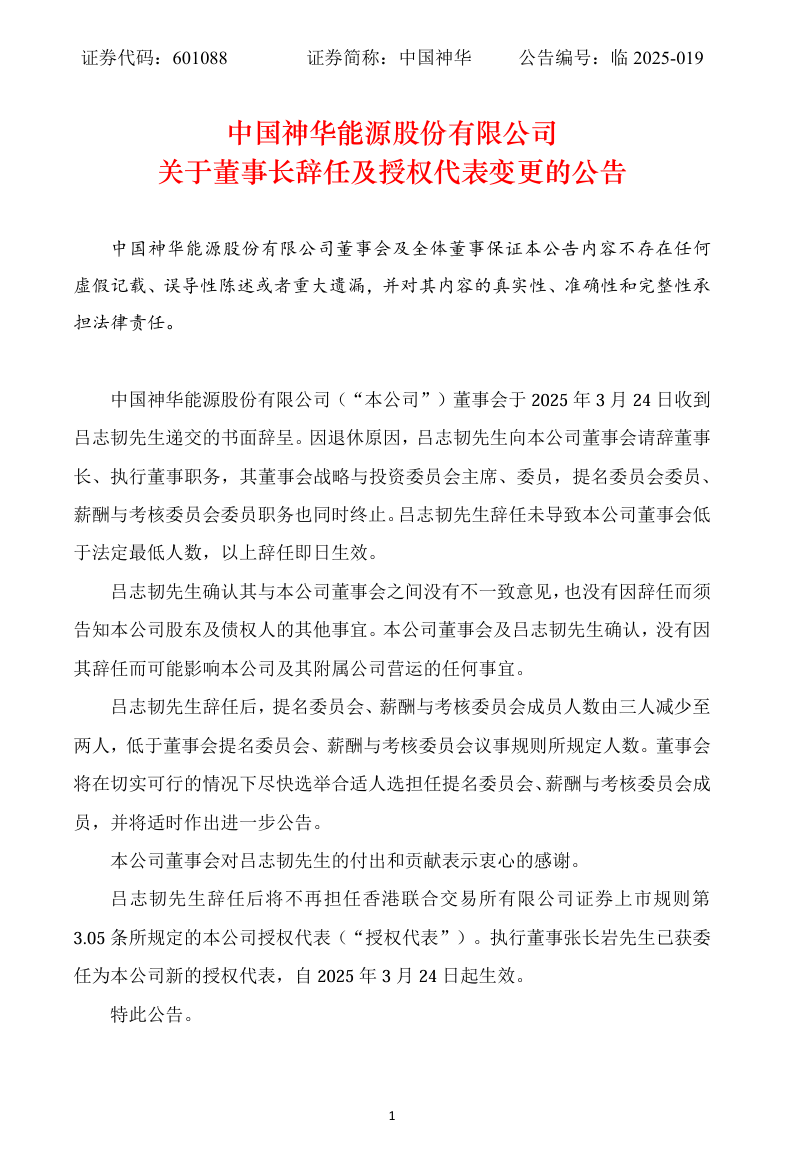北京时间3月12日消息,人类能否依靠核能将净碳排放削减至零,即实现所谓的“净零排放”?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从切尔诺贝利到福岛,两次7级特大核电站事故或许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核能与核技术所面临的挑战。

1953年,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提议创建一个国际性的原子能机构。其中有一句话这样说道:“仅仅从士兵手中拿走这种武器是不够的。必须把这种武器交到那些知道如何剥去其军事外壳,并使之用于和平事业的人手中。”这段话值得我们铭记。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发生过两次7级特大核事故:2011年3月11日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以及1986年4月26日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
2011年3月11日,日本本州岛附近发生了震级超过9级的地震,随后导致了大规模的海啸,最终造成约1.93万人死亡。海啸还横扫了福岛第一核电站周围的防护海堤,随之而来的洪水导致三个反应堆堆芯部分熔毁,引发火灾和爆炸。再往前追溯25年,在苏联乌克兰的普里皮亚季,一系列人为失误导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熔毁,掀翻了一个核反应堆的屋顶,向整个欧洲释放了核辐射。
如今,核电供应了全球约10%的能源,低于2010年的13%。这一下降趋势可能还会继续,尽管在未来几十年里,核电仍将是全球能源结构的一部分。随着化石燃料时代的结束,核电能否在能源供应的减碳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1953年艾森豪威尔的联合国大会演讲之后,许多人都对核电的前景充满信心,但随着一次次核事故的发生,这种乐观情绪逐渐消失。直到今天,艾森豪威尔的讲话仍然提醒着人们,核能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着相同的来源,而这也阻碍了核能作为一种普遍能源的远大前景。
在中国和印度等国,新的核反应堆仍在计划和建造中。但是,正如国际能源署(IEA)所指出的那样,核能的总体吸收仍低于其所谓的“可持续发展情境”,特别是在高收入国家。而且,由于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不断降低,未来对核能的需求可能并不会反弹。
当核灾难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时,很难想象人们曾经对核能抱有多么大的热情。当时,许多人将核能视为应对全球能源需求的重要方式之一。从1951年第一座实验性核反应堆开始,新的反应堆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不断增加,并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达到高峰,几乎每年都有20至30座反应堆投入运行。1957年,在英国坎伯兰(现坎布里亚郡塞拉菲尔德)西北角的温斯乔反应堆(后来改名为塞拉菲尔德)发生了一场火灾,但这场英国史上最严重的核事故并没有阻碍全球核能产业的增长。
到了197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三里岛核电站发生事故后,情况发生了改变。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冷却系统出现故障,导致反应堆堆芯部分熔毁,放射性物质发生泄漏。幸运的是,这场事故并没有导致任何生命损失,但在7年后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有31人直接牺牲,在当时的苏联、东欧和西欧,还有数以千计的人受到辐射影响,但具体伤亡人数仍存在争议。在福岛核灾难中,多达50人遭受了非致命的辐射灼伤,1人随后死于辐射暴露导致的肺癌。
除了死亡和健康风险,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造成的损失据信超过2000亿美元,而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估计,清除福岛核污染的成本在4700亿美元至6600亿美元之间。2011年的灾难发生后,日本有12座核反应堆被永久关闭;另有24座反应堆目前仍处于停运状态,等待正在进行的安全审查,这无疑也增加了大量成本。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在建设成本之外,任何投资核能的国家都必须做好准备,预留足够的资金,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灾难,无论是由于人为错误还是自然原因。
计划开展核能项目的国家还应该与核供应国集团(NSG)和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合作,前者主要负责监督和管控和平目的的核贸易,后者则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IAEA并不是传统的能源监管机构,它不仅负责监督和检查核电站,同时也在努力确保核裂变材料不被某些国家用于武器用途。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一些国家——如印度和巴基斯坦,很可能还有以色列——在最初寻求用于研究或开发核能的核技术后,进一步成为了核武大国。
考虑到核能利用在技术上的种种壁垒,世界上大部分核能还是由核武器国家所生产。另一方面,如果建设核电站的总费用高达数千亿美元的话,大多数国家都会表示拒绝。相比之下,可再生能源技术尽管仍处于相对起步的阶段,但其成本正逐渐下降,监管也更加直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这些新的技术不需要涉及与国家或国防有关的设备。
很显然,核能还将伴随我们一段时间:新核电站正在建设中,旧核电站退役还需要一段时间。不过,事实证明,核能并不是曾经被视为世界能源市场减碳的解决方案。核能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其持续性的低使用率表明,一些国家认为发展核能的风险超过了收益。对另一些国家来说,发展核能是一项难以负担的事业。如果世界要实现碳净零排放,就必须将重点放在可再生能源上,因为这些能源的最大优势之一,便是几乎所有国家都可以免费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