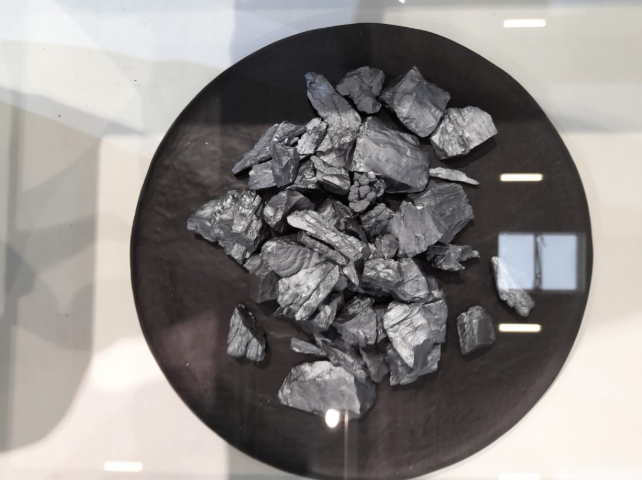德国一直以来都是全球“退煤先锋”,但近期受天然气供应危机影响,重启1000万千瓦封存煤电机组,并考虑将另外600万千瓦煤电机组作为紧急备用,重启总规模可达1600万千瓦,占德国总装机容量的7.0%。同时有消息称,德国政府考虑再次将煤电关停时间由2030年延缓至2038年。德国退煤“开倒车”受到各界广泛关注,引发对其碳中和进程大倒退的猜想。详细分析德国退煤思路可以发现,重启煤电是德国保障能源安全的既定政策,是退煤大趋势下的小调整。进一步剖析欧美典型国家退煤过程不难发现,打造自身优势清洁能源产业、“先立后破”,是美国、丹麦相比德国煤电转型更加平稳的主要因素。
欧洲一直走在全球能源转型前列,但当前天然气短缺导致的电力短缺问题,也间接反映了欧洲可再生能源的增产、扩供与天然气进口之间的失衡。短期来看,灵活性资源配套不足等客观条件限制使得可再生能源短期内难挑大梁。尽管欧洲可再生能源已进入规模替代阶段,但前期储能、需求响应等新型调节能力发展不足,造成风电、光伏面临有电供不上的局面,德国近几年弃风率已攀升至接近5%。长期来看,当前的能源危机,尤其是天然气等化石能源严重依赖进口导致的危机,使以德国为代表的很多欧洲国家更加坚定地认为,应进一步加快发展本地化的可再生能源,并广泛实施限价、补贴、减税等举措来继续刺激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发展。
丹麦打造国有清洁能源企业实现“产业替代退煤”。在明确利用风电和生物质热电联产替代煤电的转型战略后,丹麦政府积极牵头开展优势能源企业重组,通过统筹和优化资源配置,助力企业实现从“黑色”到“绿色”业务的平稳过渡,进而利用产业替代,推动实现国家退煤目标。2005年,丹麦政府将本土6家电力公司合并成为政府控股81%的DONG能源集团,通过资源整合,DONG拥有了3个大型海上风电场。此后DONG明确了到2040年将化石能源业务全部转为可再生能源的转型战略,并在关停煤电项目或开展生物质替代的同时加速扩张海上风电业务。如今,DONG已经成为海上风电的头部开发商,全球市场份额高达25%。
美国通过严控排放标准、建立多元竞争市场、扶持优势页岩气产业构建立体退煤体系。立足自身资源优势和能源独立目标,美国将制定污染物排放标准作为退煤的重要政策抓手,将非常规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产业作为发展目标,遵循市场化竞争规律落实退煤。自20世纪90年代起,美联邦政府陆续出台了针对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粉尘、臭氧、汞等污染物的精准排放控制条例,导致新建煤电项目的固定投资成本一度飙升至气电的2.4倍,大量现役机组因不愿或无力安装环保设备而选择关停。与此同时,政府通过给予非常规天然气产业长达31年的补贴,带动页岩气以每年1万亿立方英尺的速度增产,气电成本快速下降。据统计,在美国累计淘汰的1亿千瓦煤电机组中,有80%是过去十年关停的,这意味着在市场化竞争环境中,气电和可再生能源发电正在快速替代美国煤电的发展空间。
处理好政府、市场和产业的关系,在壮大优势清洁能源产业过程中实现煤电转型。一是发挥政府在煤电转型中的目标引导作用,用好制定煤电发展目标、加强污染物排放标准、提供经济补偿和整合企业资源四大抓手,保障退煤方向不跑偏和目标可落地。二是市场化竞争是推动煤电转型的主要手段,通过各种发电资源与煤电充分竞争,保障煤电退出的经济性,防止资产沉没,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确保退煤的可持续性。三是发展壮大优势清洁能源产业是退煤的基础,美国、丹麦依托优势清洁产业保证了退煤的平稳,而德国则由于缺乏清洁能源产业根基,退煤呈现“螺旋式”前进。
处理好安全、发展和减排的关系,保障煤电平稳、有序退出。一是必须重视煤电在电力系统中的安全兜底作用,做好电力碳中和长期谋划,明确各类电源定位,制定应急储备预案,加快探索储能、需求响应、电制氢等商业化模式。二是提前谋划煤电基础设施融合复用,不仅要挖掘既有基础设施清洁利用潜力,推动煤电与供热融合发展,而且要提前谋划煤电厂向生物质热电联产或电制氢工厂改造升级,发挥退出煤电厂基础设施的复用价值。三是客观认识煤电碳排放问题,煤电减排与煤电发电量相关,增加煤电装机并非等于增加碳排放,要做好退出煤电的封存方案。
处理好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关系,防止“运动式”退煤和煤电“冲高峰”。一是立足当下高度重视煤电支撑性调节性作用,把大力推动煤电灵活性改造作为煤电存量机组转型的核心路径,避免替代能源顶不上而“未立先破”、把长期战略当作短期任务等走偏的行动和认识。二是必须坚定认识煤电逐步减量是长期不可逆转的趋势。煤电是各国碳排放的主要源头,碳中和目标下煤电减量替代是各国能源转型的必然趋势。虽然经济发展和能源安全形势不断演变,但不能认为煤电仍能“冲高峰”,把短期形势误解为长期趋势,把应急措施当作长期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