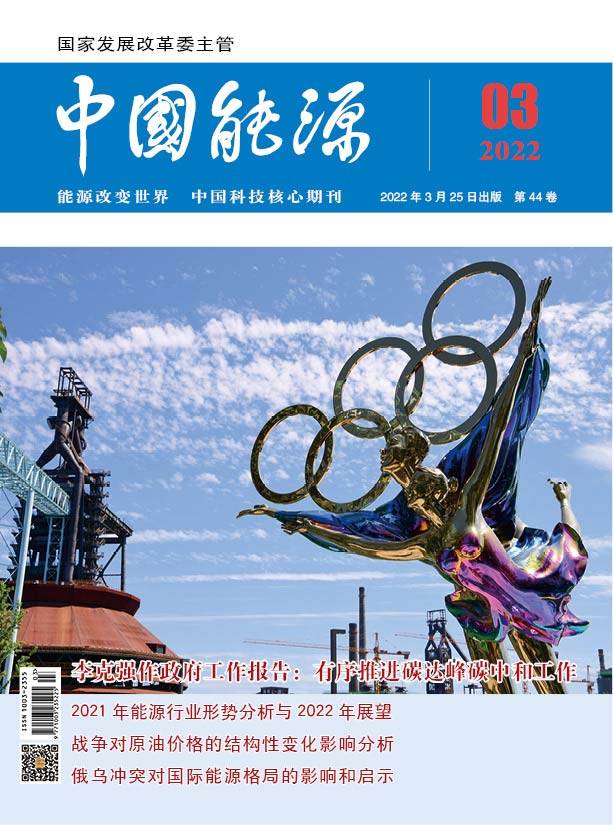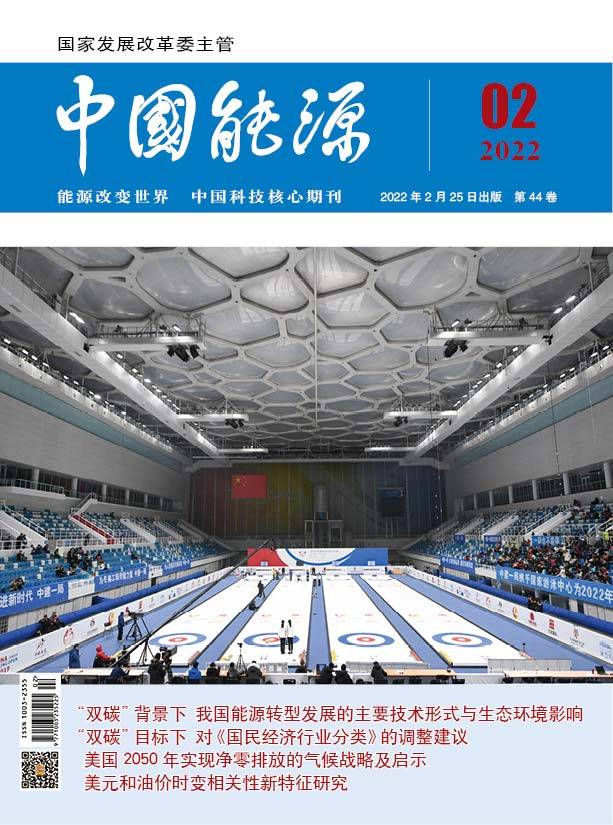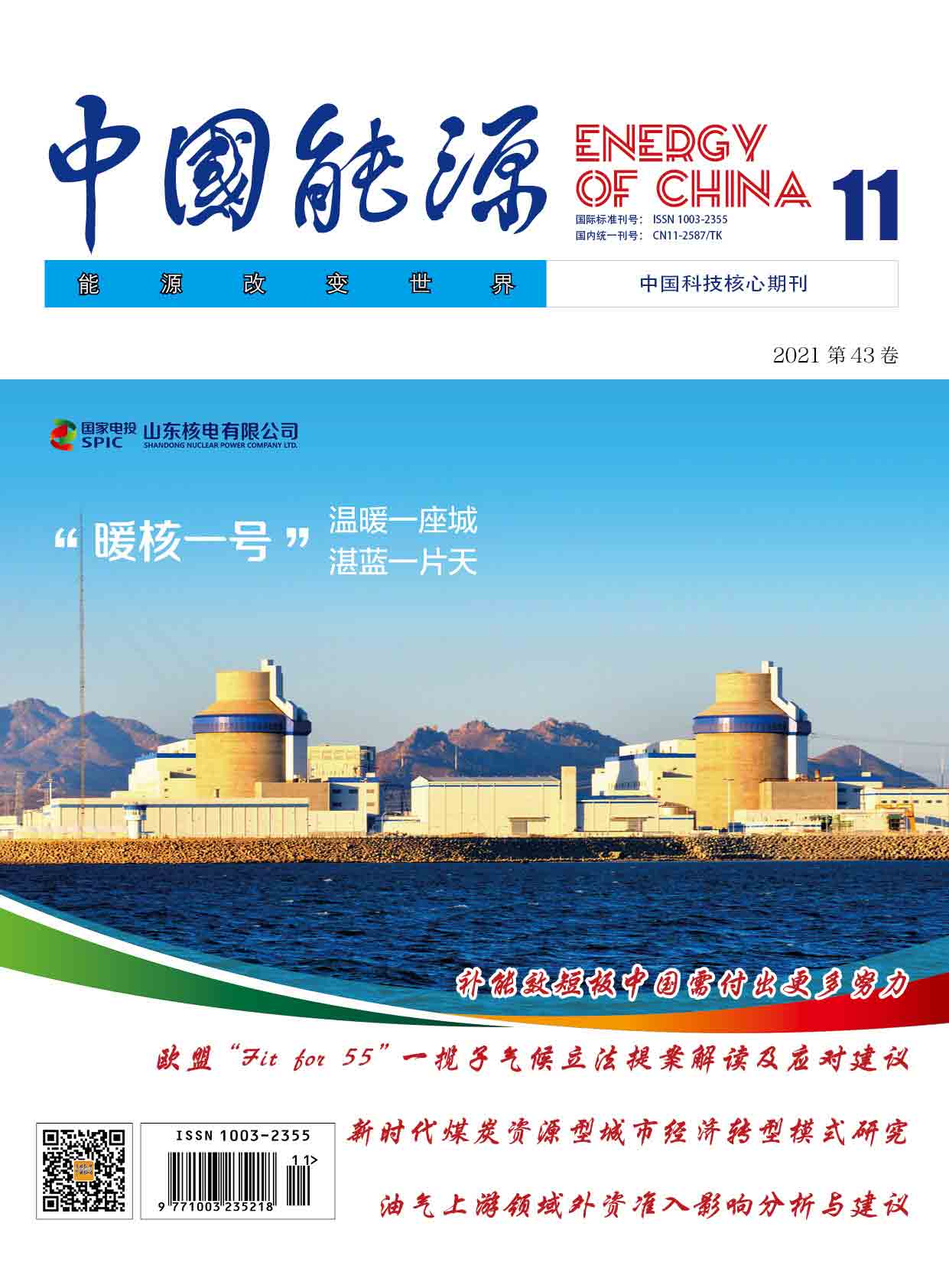一、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的出台背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钱自己办——少出钱请人办——不出钱只放权”等多管齐下,打造我国公共支出和公共服务的现代治理体系
2015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的重大调整,中国经济转型有望迎来实质性突破。中央之所以现在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原因在于单纯的需求管理难以助推中国经济“爬坡过坎”。
供给侧改革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公共部门不能盲目自信。近年来,不管是对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还是新能源汽车的推广,政府部门都推出了大量的财政补贴。然而,这些财政补贴不少“沦为”了企业的“唐僧肉”,企业伪造能耗等相关数据骗取补贴、套取补贴的案例并不罕见。大量低效、无效财政补贴在扭曲市场资源配置的同时,还加重了有效市场经济部门的财税负担。人们经常会关注税收的效率损失(deadweight loss),事实上政府补贴等有违非歧视原则的财政补贴的效率损失同样不容忽视。因此,推进供给侧改革,要求政府部门从不可持续的“财政刺激陷阱”中主动解脱出来。一定规模、一定时点的财政刺激政策,确实可以使经济企稳回升;但是长期大规模刺激、超越了最佳临界点,其边际效应必将不断减弱,甚至会形成“刺激效应越减弱——刺激规模越扩大——市场经济部门税费负担越重”的恶性循环,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不断扩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减轻企业税费负担”。
同时,2014年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 “新常态”,突出表现为“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与我国社会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相伴随,我国财政收入正由高速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如果按照“以收定支”来谋划,新常态之下中低速增长的财政收入也将难以支撑过去政府部门“以我为主”的财政支出“高举高打”。
20世纪80年代财税体制改革的主基调是“放权让利”,当时财税体制改革的前提是集中过度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且后来分权过度之后,1994年分税制改革又提出了提高全国财政收入和中央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我国2014年财政收入的22%左右的比重基本合适,也为了避免“来回折腾”,这样我国当前供给侧财税治理改革的基本思路就非常清楚了,那就是“简政放权”。
为此,我国先期已经进行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等改革,以撬动社会资本,同时为政府“瘦身”。此外,还可以充分发挥碳交易(cap and trade)、排污权交易、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特许经营(concession)等市场化交易机制的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既保证了相关公共产品的提供,又防止政府规模的借机扩大、防止政府越俎代庖。总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出钱自己办——少出钱请人办——不出钱只放权”等多管齐下,打造我国公共支出和公共服务的现代治理体系。
二、以更宽广的视野来认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未必一定能够如人所愿。2016年4月出现的魏则西事件清晰地向人们表明,政府公共部门关注的是公共利益,而社会民间资本更关注的还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果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等模式简单粗暴地将社会资本嵌入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过程,那么社会资本很可能“狐假虎威”,获得了谋取更大私人利益的“抓手”,进而扭曲公共产品的提供,从而损害社会整体利益。为此,对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不能放任自流,必须加以规范和限制。尽管政府部门是在公共利益轨道上“公转”,而社会资本在私人利益轨道上“自转”,二者看似风牛马不相及,但是让社会资本在私人利益轨道“自转”基础上,将其纳入政府部门“公转”的“星系”,则有望实现政府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双赢”。
当然,对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我们还需要有更宽广的视野。如前所述,此次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被提出的背景是2014年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遇到的“新常态”。也就是说,2014年以前,这一问题并非如此迫切。上溯至2001年我国“入世”以来,我国成为“世界工厂”,成功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使我国充分分享了经济全球化的“大蛋糕”。当时一是政府财政收入充沛;二是社会资本主要分布在出口部门经济领域。然而,现在时过境迁,全球经济不景气导致我国外需不振,政府部门、特别是地方政府部门“撸胳膊挽袖子”亲自来到了“稳增长、调结构”的第一线,通过地方融资平台集中了大量资金。这时的社会资本面临既无“源水资金”、又无“投资项目下锅”的窘境。因此,归结起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要想健康发展,首先需要处于“强势地位”的政府部门在一定程度上“放手”、“让位”,给社会资本以更大的“用武之地”。2016年底以来,美联储在金融危机之后开启了“缩表”进程,即要压缩其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执行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为其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减费”,标志着其货币政策的“转向”。与此相呼应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启动了“减税”计划。如果将政府财政收支看成是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的话,特朗普“减税”就是政府财政收支的一种“缩表”尝试——当然在强大的政治压力面前,这种政府财政的“缩表”并一定能够轻易成功。实际上,不管是央行的“缩表”、还是政府财政的“缩表”,都不一定是绝对的,相对“缩表”更为常见。也就是说,央行货币发行和财政扩张的步伐只要相对慢于经济增长,就是一种“缩表”。我国生活在“地球村”当中,我国早在2015年就提出以“三去一降一补”为核心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为标志,国家加大了对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工作力度。这就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可能。
可见,今天我们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关注的核心问题依然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政府与社会资本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同时又如“自转”与“公转”一样浑然一体,而不能你只有我、我中有你,浑水之后必然会有人借机摸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