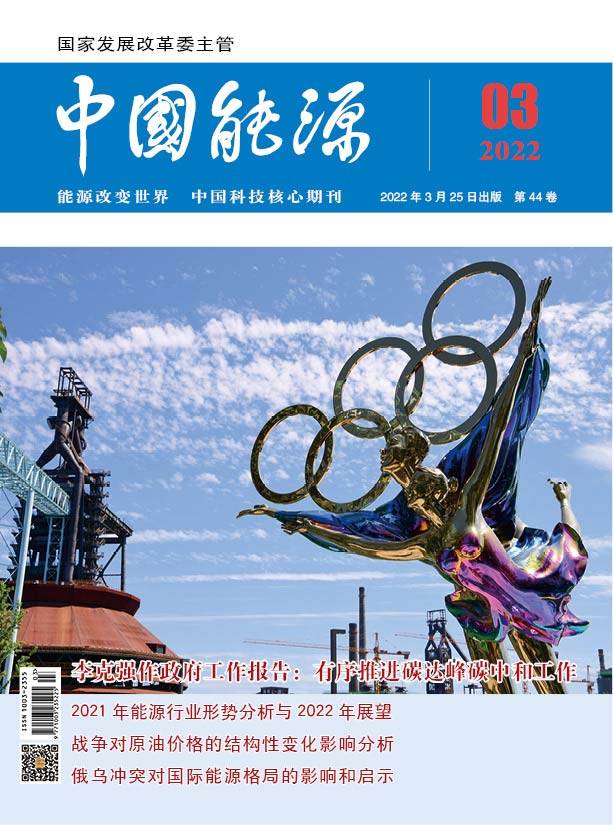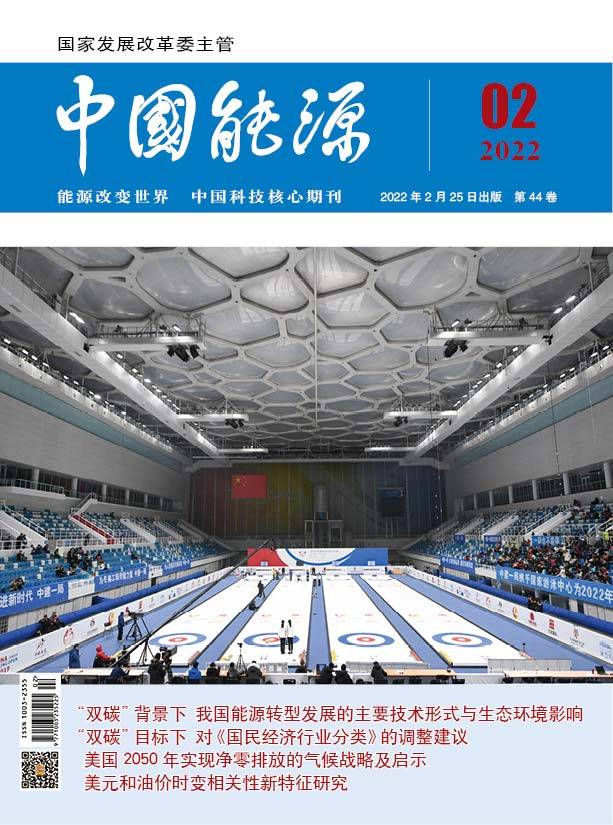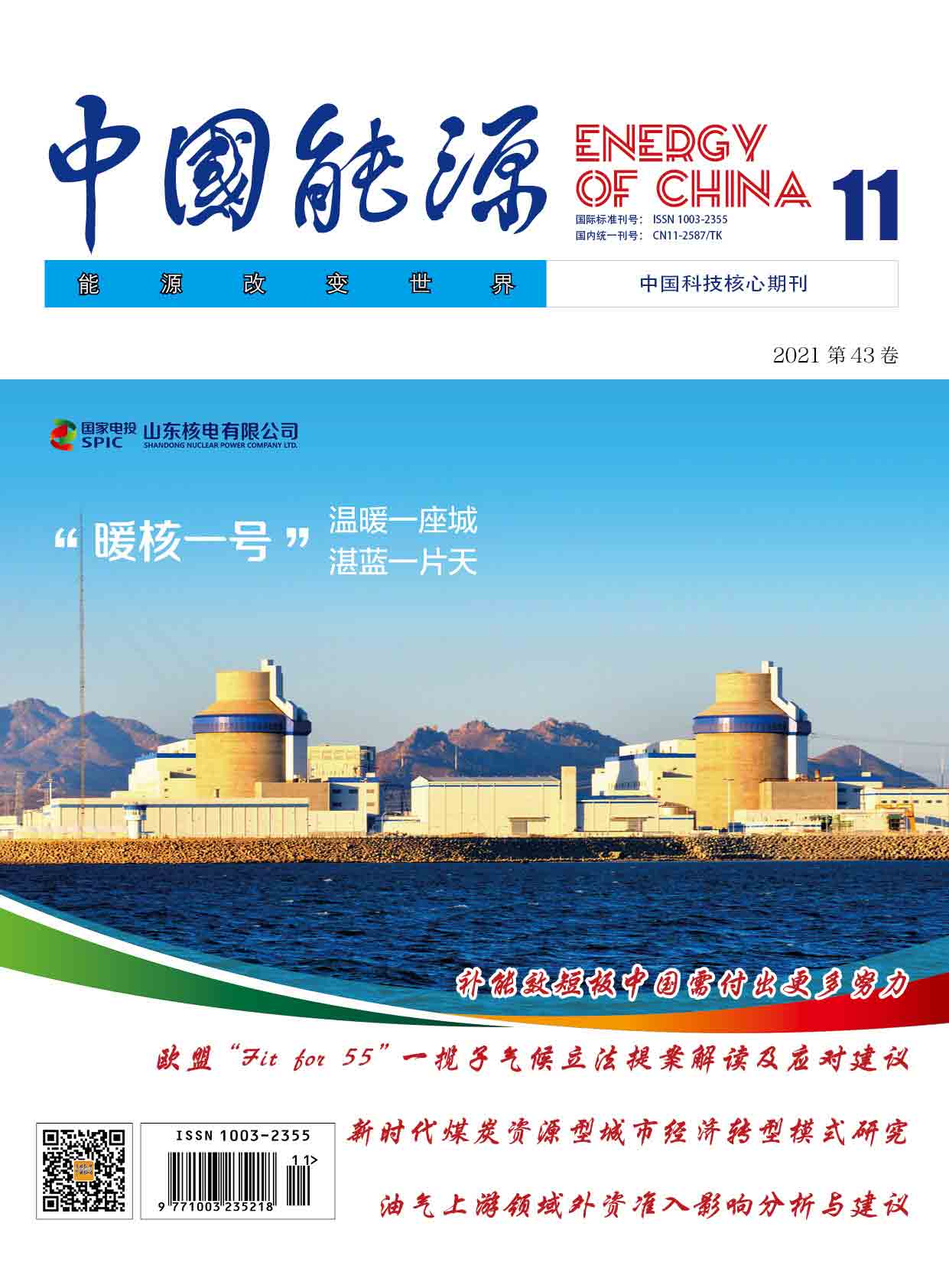12月,国家发改委和农业部联合出台《关于推进农业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截止到目前,已经有住建部、交通部、农业部、国家能源局、环保部、文化部、工信部、国家林业局等部门在各自的专营领域内,发布了推进PPP的指导意见。
紧接着,全国财政系统PPP工作推进会暨示范项目督导会在云南昆明召开。会上披露截至今年10月末,财政部PPP综合信息平台入库项目10685个,总投资12.7万亿元,其中进入执行阶段的项目1014个,总投资1.72万亿元,落地率26.8%。仅6~10月就新增落地项目395个、新增项目总投资6600亿元,项目落地速度明显加快。
但会议最大的看点却是强调了目前PPP正在面临突破“瓶颈”,首当其冲就是立法问题。据了解,反映比较多的问题是法律保障待加强。由于缺乏专门立法,PPP项目各个环节如何适用现行法律不尽清晰,相关各方利益难以顺利通过法律途径得到明确保障,社会资本对PPP政策的稳定性和项目长期运营心存顾虑。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中心联席主任邓峰看来,法律保障和产权问题解决是PPP尽快推进的关键,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是两个大力推进PPP的部门,各自先后出台了多个文件、通知,来推动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部门的PPP进展,但两部门的理念差异如何协调还待解决。
PPP的制度困境
“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对PPP高度热情,财政部几乎每周都出新文件,发改委也在以同样的频率制造文件。”邓峰认为。

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还各自组建了一个专家库。据公开报道,国家发改委的专家库有343名专家,财政部的专家库有200多名。其中,一些人还成为双库专家,比如济邦咨询董事长张燎、大岳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金永祥、毕马威咨询(中国)有限公司合伙人邢佶勇、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周兰萍、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飞等。
邓峰表示,狭义上的PPP,按照“谁出钱”,可以分为公共服务外包(contracting out,公共部门出钱,私人部门干活)和私人资金进入(contracting in,私人部门出钱,私人部门执行)。目前而言,财政部强调更多的是前者,强调资金管理,用物有所值来进行控制;而国家发改委的视角更多靠近后者,用强制竞争性要约(CCT),即招投标来控制。
“从法律上看,立法者现在认为PPP的焦点问题是主导权应该掌握在谁手里,司法者的角度焦点在于这是一个行政合同还是民事合同,中央政府的立场是考虑如何确保地方政府的信用能够得到提高,能够在履约过程恪守合同。”在2016中国环保上市公司峰会上,邓峰表示当前各种讨论应回到问题的根本。
一般来说,PPP项目的周期长达10~30年,所以很多受访企业表示担心政府、领导人换届后不承认“旧账”。
中央层面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11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公布,其中第七条为完善政府守信践诺机制,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严格兑现向社会及行政相对人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将政务履约和守诺服务纳入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建立政务失信记录,建立健全政府失信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加大惩戒力度。
同期,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规定对政府违反承诺,特别是仅因政府换届、领导人员更替等原因违约毁约的,要坚决依法支持行政相对人的合理诉求。对确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改变政府承诺的,要依法判令补偿财产损失。
不过,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刘敬霞认为,这些文件还没有理清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协议的合同性质。《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十一项将涉及“政府特许经营协议”的诉讼列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后,出现了同样的项目合同名称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协议”的就是民事合同,但是叫“特许经营协议”的就定性为行政合同。如果是民事法律关系,社会资本就可以按照民事诉讼程序保护权利;如果是行政法律关系,就是行政诉讼,政府很容易推翻授予社会资本的权利。按照国家赔偿和按照民事合同约定赔偿,有天壤之别。刘静霞是在中国民营企业平等保护论坛——落实中央《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研讨会发表这一言论的。
在邓峰看来,我国最早开展实际PPP模式的高速公路领域,存在很多失败经验——要么是投资方获得暴利,在合同规定的运营期还未满的时候,投资方早已收回投资并且获得超额收益,而政府就想办法减少这种暴利,再修一条高速公路或者国道竞争;要么就是收益过低、投资方受损,投资方想方设法要求政府延长运营收费期,或者要求政府回购资产。
邓峰认为,产生这些违约、纠纷的关键就是对收益的预测不准确,因为运营年限是按照预测收益来设定的。
“预测不准不是更多专家、更科学的办法可以解决的。当年建设首都机场T2航站楼,专家预测可以用到2020年,现在看来,T3航站楼都不够用到2020年。”邓峰建议,改变招投标的机制,比如国际上比较优秀的最小净现值拍卖法。
现在拍卖是通过招投标制度,一条高速路,专家预测收益和修建成本,投资方在投标时要表示愿意用多少成本、大概获得多少回报。邓峰介绍,此前政府允诺的收益率通常是8%~12%左右,现在发改委提到15%,以为这样就能解决问题。
邓峰建议,如果一条高速公路规划投资20亿元建设,投标者在标书中提出投资规模和回报率,要求回报率最低者中标。实际可能花了30亿元,要求回报率为3%,这条路上有多少人通行可以监控,收费到31亿元,资产交付政府,没有固定期限,完全按收益成本核算。
“PPP要想真正起到促进社会效率的作用,需要在未来的规则中,根本性地解决合同法问题、用户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招投标问题、政府的信用问题。”邓峰对PPP的前途展望乐观,“因为已经有非常多的国家理论研究摆在前面。”
PPP大热的背后,是“稳增长”的积极要求。随着房地产政策调整,市场预期2017年房地产投资的增速将有所下滑,基础设施很可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扮演重要角色。
12月14日发改委数据显示,仅11月单月就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26个,总投资2642亿元,项目主要集中在交通、能源和水利领域。
这些领域正是目前PPP主要的推进领域。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住建部海绵城市专家委员会委员、财政部环保部等PPP推荐项目专家满莉坦承,推PPP的目的之一是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用好杠杆、盘活存量,“财政不可能再当冤大头、买单王了。”在满莉看来,在中国,PPP不只是推动实现现代国家治理的工具,还是平衡中央和地方、部委和各部门之间的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利益协调机制。
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会长、博天环境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赵笠钧认为,政府现在缺钱,所以要引进社会资本,但是如何安排才能综合成本更低、效益更好,制度上是不清楚的。
邓峰认为,在清理完毕地方债后,《预算法》又捆死了地方政府的借债能力。“到目前为止,连续起来看财政部所颁布的文件,比如禁止明股实债,不能把BT、BOT换个包装就进来,就能看出它的摇摆心态,又想松绑,又怕出现新一轮的地方债。”
“通过PPP,政府可以把债务转化成企业债,通过多年经营和展期,将债务分摊到多年来实施。”安信证券环保分析师邵琳琳在水生态安全大会上表示。
12月7日,发改委投资司副司长韩志峰透露,发改委投资司和财金司正在研究设立PPP专项企业债券,开发出适合PPP项目特点的企业债券,以更好地降低PPP项目融资成本。这一信号释放了通过市场化手段寻求PPP项目融资突破的可能。
金融机构的反应很快。 一位机构人士向媒体表示,一得到监管层正研究推出PPP专项企业债券的消息,公司相关部门研讨已经开始,目前来看,以项目收益债的形式发行可能性较大。不过他也表示,这个口子一开,仍需许多政策配套,比如发行、准入制度要改变。债券中间的配套措施也需要跟上,比如评级,不能照搬城投债的评级,需要建立新的评级规则等。
赵笠钧看来的理想模式是,政府发债,请专业公司提供专业服务,通过DFO(design field operation)的模式,这样双方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我想政府在设立一个制度的时候,要考虑终极解决什么问题,PPP是解决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问题,应该在这个目标下所有要素达到最优配置。”
赵笠钧认为,政府希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能够社会化运营、解决政府部门管理的高制度成本,比如污染治理项目,政府自己建设自己管理,环保监管不容易实施,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一直在积极推动环境第三方治理,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的第三方治理不一定就是社会资本,资本可以政府出,但是建设管理要交给社会化公司。”赵笠钧表示。
瀚蓝环境总裁金铎和邵琳琳都认为,PPP的推进可能会给行业带来巨大变化,民企可能更多的要寻求和央企、国企合作,以便获得更好的资金来源和人脉关系,中小企业可能从过去直接面对客户变成通过平台企业和客户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