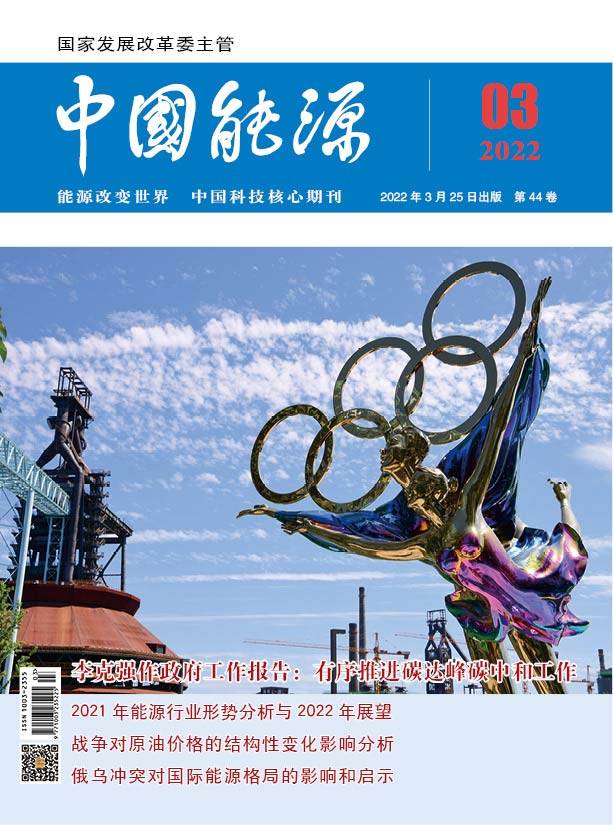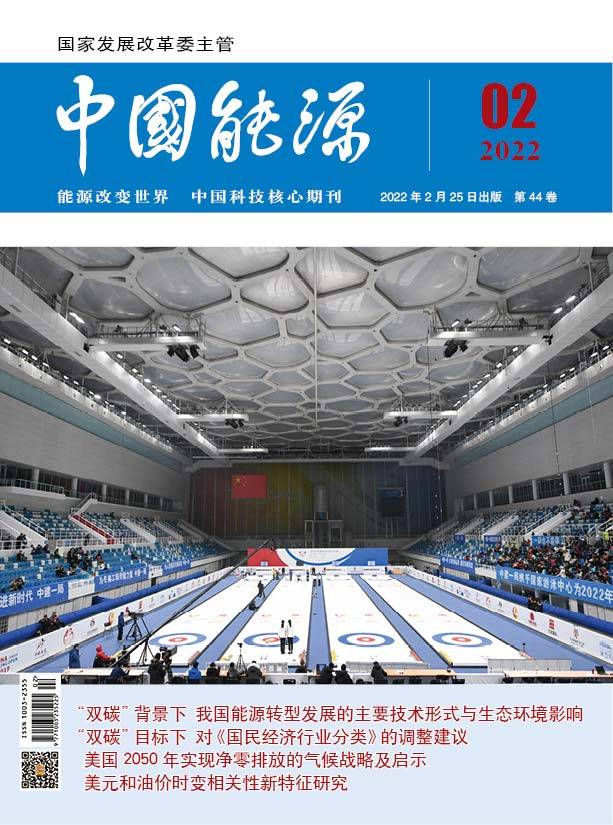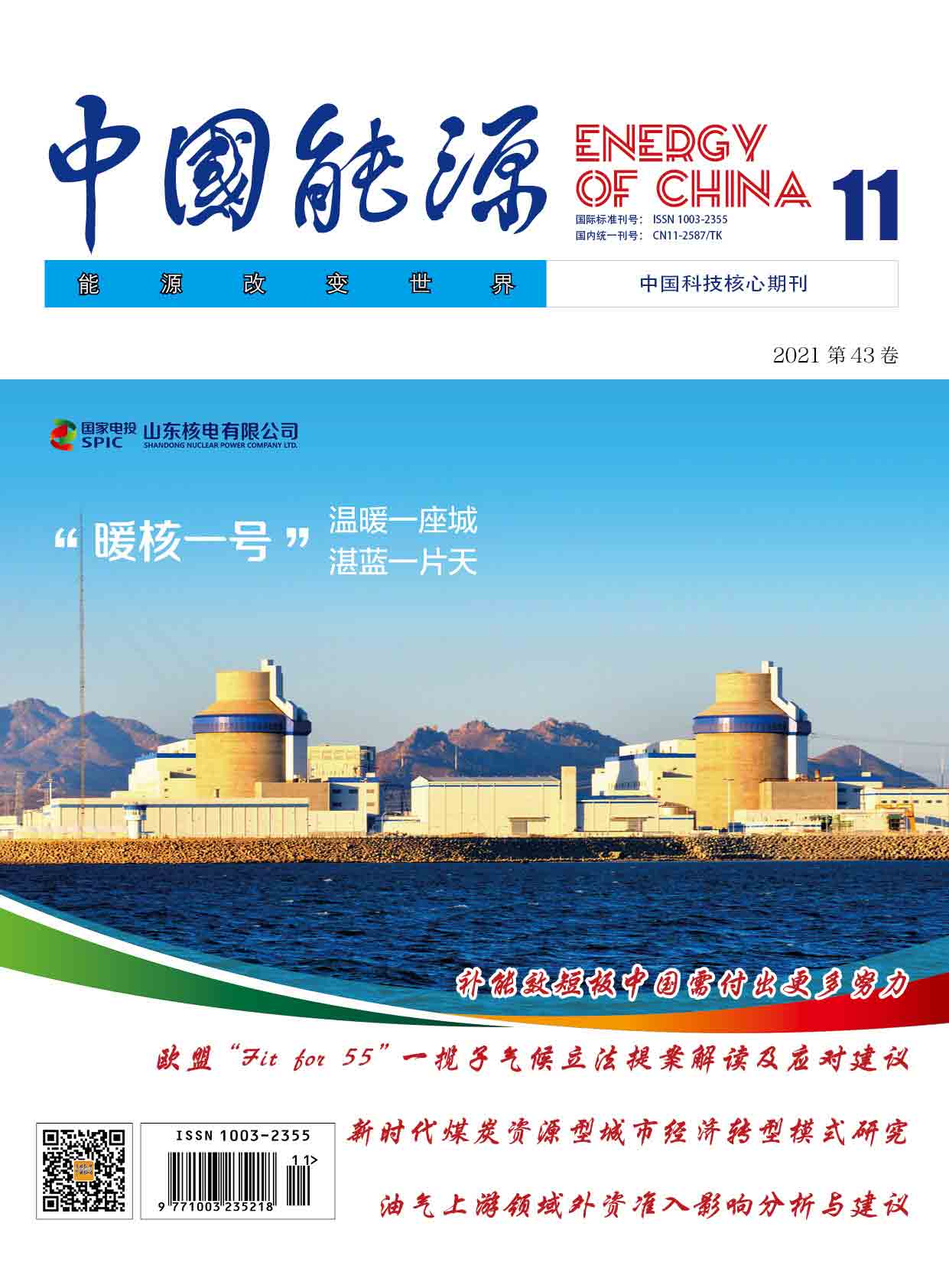10月的一天,德国西部城市博特罗普的郊区阳光明媚。沿着一条安静的公路,我来到了绿水青山之间的一处无名之地。高速公路在不远处蜿蜒。此处最吸引眼球的是一个带有4个巨大轮子的A型建筑——竖井井架,用来将工人和设备运输到井下。这个竖井井架也是唯一可以直观证明在1200米的地下有着德国最后的硬煤的证据。
博特罗普坐落在鲁尔谷,鲁尔谷是一个拥有550万人口的地区。这里曾经有近200个煤矿,每年能生产1.24亿吨煤,有超过50万矿工在煤矿工作。
明年,随着这里最后一个煤矿的关闭,一个时代即将终结。鲁尔谷正处在转型之中。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一个个煤矿和钢铁厂逐步关停。在德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努力下,一个又一个风力涡轮机在老式竖井和焦化厂之间竖立起来。
但是从煤炭转向清洁能源的道路并不是一马平川的。博特罗普的Prosper-Haniel煤矿所发生的一切正是德国和全球其他煤炭生产国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的一个缩影。
放眼全球,随着各国政府逐渐淘汰曾经被称为工业粮食的煤炭,越来越多的煤矿正在陷入沉寂。如果想让退休的煤矿为下一场工业革命提供动力,那就得抓紧时间了。
那些将德国最后的矿工运输到矿井的罐笼,每小时的速度接近48公里。“这速度跟城里的摩托车差不多。”鲁尔矿业财团的公共事务官员克里斯托夫-贝克(Christof Beicke)说。这个说法让人有点不寒而栗。
我与一群游客一同走进罐笼,门在关上的一刹那发出了吱呀的声音。
罐笼缓缓下降,在我的胃部一阵痉挛之后,伴随我们的只有通过罐笼栅栏吹进来的湿冷的风和轰隆隆的声音。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停滞,几分钟就像几个世纪那么漫长。
罐笼最终停了下来,停在这个矿井的最深处——第七层,我们进入了一个看起来与地铁站台相似的房间。参与建造这个井巷的工程师哈马赞-阿特利(Hamazan Atli)带领我们这一群游客穿过了大厅。站在荧光灯下,微风拂面,机器的轰鸣声不绝于耳,我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仿佛走进了一个人类智慧的终极产品之中,比如一个太空站或者一个潜水艇。
单轨火车是我们通往煤层的交通工具。大概半个小时之后,我们走下火车,将安全帽上的灯打开。这里的温度明显升高了。当我们沿着有点倾斜的路向采煤工作面走去时,空气中弥漫的硫磺味儿越来越浓烈。我们弓腰前行,一架架液压支架保护着我们,使得顶板不会掉下来砸到我们身上。
因为这里煤层的高度只有1.5米,所以当我们穿过时,不得不弯着腰。地面的积水很深。采煤机今天没有工作,因此我们没有看到采煤机将煤割下来,再通过皮带输送出去的场景。
今天的矿里十分安静。两个满脸煤灰的矿工从我们身边挤了过去。当我们在液压支架旁边坐下来的时候,煤层上方的顶板偶尔会掉下一两块石头。
后来,在明亮的房间里,克里斯托夫-贝克问我有什么感受。我说这里真是极端的人类环境。他点点头说:“是的,这里像是被时间遗弃的地方。”
鲁尔谷拥有53个德国曾经最强大的工业中心城市,包括埃森(Essen)、波鸿(Bochum)和奥伯豪森(Oberhausen)等。这个地区曾经是低洼的河谷地带,但是现在一座座小山随处可见。这些小山都是从矿井中开采出来的煤矸石。
由于许多煤矿已经关闭,这些矸石山上长满了杂草。在埃森郊区的一座山上,一边放着15米高的雕像,另一边巨大的风力涡轮机就像一朵朵机械雏菊一样绽放。
德国被誉为全球清洁能源转型的领导者,自2002年以来,德国在可再生能源补贴方面已经花费了2000多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平均每年花费200亿美元来补贴化石能源)。
为了让德国摆脱化石能源和核能的束缚,2011年,默克尔政府宣布开始实施“能源转型”(Energiewende)政策。去年,包括风能和太阳能在内的可再生能源为德国提供了近30%的电力。“能源转型”的目标是到2020年,让可再生能源占到德国能源消费总量的40%,并让碳排放量较1990年减少40%。
这种转变意味着鲁尔谷生态环境会逐步好转。现在每一座拔地而起的矸石山都意味着地下有体积更大的煤炭和石头被挖走。该地区整个地表已经下沉了约24米。
流进鲁尔谷的河流无法从另一端流出,贝克解释说,现在河水都在从未到过的地方形成水池。煤炭公司负责将那些水抽走,并将该地区的地下水也抽走,以保证地下水位低于现有矿井的水平。废旧煤矿里的脏水也必须得抽走,以免污染地下水。
而这只是煤炭公司必须永远不断重复做的事情中的一件而已。
贝克说,只要那五六百万人还想在这个地区生活,煤炭公司就得天天如此。“也许2000年后情况会有所改变,但是现在只能如此。”他说。
德国政府每年会向矿业联合会提供2.2亿欧元的补贴,以应对煤炭开采产生的所有问题。与美国的老旧煤矿经常会被出售或者宣布破产然后就无事一身轻不同,这里的煤矿即使关停了,煤炭公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必须处理原先的废水。
尽管德国政府承诺进行较为彻底的能源转型,但现在很多人都认为,由于某些经济和社会因素,比如很多地方继续使用褐煤来发电,德国不可能实现其制定的可再生能源目标。德国的人均电力消费成本是欧洲国家中最高的。
如果德国继续朝可再生能源目标努力,那么新能源肯定主要来自于风力。德国的风力涡轮机比欧洲其他国家都多,其中许多风力涡轮机都是在过去六七年内安装的。但是风力发电具有很大的间歇性,这对于电网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因为即使电力供应短时间中断,也有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
随着越来越多的风力涡轮机投入使用,越来越多的燃煤电厂退役,这个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间歇性能源的存储问题成了一大挑战。这个国家的退役煤矿可能再次被证明是有用的——它们就像是清洁能源的巨大电池。
要把煤矿变成电池,需要的是重力。当然,还需要很多钱,但基本原理是重力。当你举起一个重物时,它会把将它举起来的能量存储起来,当它落下来的时候能量就会被释放出来。
拿水来举例说明。当你想存储能量的时候,只需要把水抽到高处,存入水库中。当你要使用这种能量的时候,可以让水流下来,带动涡轮机转动,这些涡轮机能将冲击转化为电力。
这就是来自埃森—杜伊斯堡大学的两位教授安德烈-尼曼(Andre Niemann)和乌尔里希-施赖伯(Ulrich Seiber)的一个设想。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法将废旧矿井利用起来。看起来他们的设想很直观:上下水库之间的落差越大,能够存储的能量也越多。还有什么比煤矿更深呢?
地质学家施赖伯意识到,将废旧矿井变为抽水蓄能水库从理论上来说是可行的,但这是一个所未有的设想。尼曼是一名水力工程师,他认为这个设想值得一试。他筹集了一些研究经费,然后花费了几年时间进行这个设想的可行性研究。他们在鲁尔谷找到了一个废旧的煤矿,并对运行成本和收益进行了分析。
在对该地区的断层和地层进行研究之后,尼曼的团队最终选择了Prosper-Haniel煤矿。他们计划在煤矿旧址建一个类似于巨大公路隧道的地下水库。水库的周长为14.5千米,全部用钢筋混凝土围起来,高度达到30米。尼曼表示,水库的一侧高度会稍微低一些,以方便水的流动。
在最大存储容量下,涡轮机可以连续运行4个小时,产生800兆瓦时的电量。
在德国,抽水蓄能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风能和太阳能都是不稳定的能源来源,具有很大的间歇性。而能量存储可以帮助满足高峰时的用电需求。当风力强劲时,可以把多余的电力存储起来。当天上的云朵遮住太阳时,存储电力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原理很简单,而且随着可再生能源的应用越来越普及,存储能源也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唯一的问题是:太贵了。
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的成本一直在下降,比起来,储能的成本却一直居高不下。尤其是修建抽水储能电站需要大量的投资。尼曼估计,光是建造地下水库,每米隧道就需要花费1万至2.5万欧元,整个项目需要5亿欧元左右。
目前,不管是政府还是鲁尔谷的能源公司都不愿意进行这种投资。
“老实说,这不是一种生意,而是一场赌博。”尼曼说。
尽管这一设想现阶段不太可能成为现实,但来自美国、中国、波兰、法国、南非和斯洛伐克等国的代表团还是到埃森拜访过尼曼和施赖伯,了解煤矿抽水蓄能的情况。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支配能源公司(Dominion)一直在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下研究这个设想。不久前,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一个小组还去埃森参观研究了这个项目。
这里,任何会在大西洋两岸引发比较的尝试都会变得复杂。在美国,联邦政府对依赖煤炭的地区的经济转型基本不插手。相比之下,在德国,转向可再生能源首先得达成广泛的共识才行。然而,即使拥有政策和公众的支持,经济上也具有可行性,只要缺乏投资,重要和必要的创新跟不上,一切都是白搭。
鲁尔谷不是阿巴拉契亚地区,不过,这两个地区有着一些关键的共同点。
煤炭被淘汰带走的不仅仅是工作岗位。生活在围绕着单一产业建立起来的社区(比如煤矿上的小区)的人往往都有一种身份认同。对于许多矿工和他们的家人来说,事情可不是打包好过去,然后找一份工作,一切从头开始那么简单。煤炭开采被视为一种呼唤、一种继承,人们希望能够将这种生活方式延续下去。
当煤矿开始裁员的时候,鲁尔谷的居民就是这样希望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以为那些美好的旧时光还会回来的,他们都这么认为。”德国煤炭协会的能源和经济学家卡伊-万-德-洛(Kai van de Loo)说,“但是它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当然,在美国,让昨日美好重现往往被政客拿来当作竞选的口号。特朗普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就曾经承诺停止“对煤炭的战争”,重振美国的煤炭产业。所以,他得到了那些产煤区选民的支持。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孟河河谷(Mon River Valley),有一个占地面积比曼哈顿还要大的井工矿发挥着超大的影响力。该州有超过8000人在这个煤矿工作,现在美国煤炭相关工作岗位一共只有5万个。而30年前,煤炭相关工作岗位曾超过18万个。
煤炭开采对于当地生态的破坏也是不容忽视的。华盛顿县东伯利恒镇镇长玛丽安-库拜其(Maryann Kubacki)说,一到下雨天,整个小镇的街道上全是黑色的脏水。
但是如果没有像德国政府那样在财政方面的支持,想改造这些煤城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宾夕法尼亚州煤田司法中心主任维罗妮卡-科谱蒂丝(Veronica Coptis)表示,组织当地居民向煤炭公司施压是一件棘手的事情。“人们不想听到你说煤炭的不好。我们想要结束煤炭开采,但是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事情。”
再说回德国,博特罗普市市长贝恩德-蒂施勒(Bernd Tischler)早在本世纪初就开始考虑如何摆脱对煤炭的依赖了。蒂施勒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城市规划师,他擅长制定长远战略。在2009年就任后,蒂施勒认为可以将博特罗普建成一个可再生能源研发中心。他设计了以从煤矿收集来的瓦斯为动力的供热厂,并使得博特罗普成为鲁尔谷第一个规划了风能区的城市。
2010年,博特罗普赢得了“创新城市”的称号,成为鲁尔谷城市的典范。据蒂施勒介绍,博特罗普现在使用的能源有40%来自可再生能源,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0个百分点。
在谈到这种转变的时候,蒂施勒的描述容易让人觉得它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在美国,煤矿涉及的问题更多,谈及此,人们往往容易变得情绪化。
对此,蒂施勒说:“在博特罗普,人们当然也害怕煤矿被关停。”但蒂施勒认为煤城有一个优势可以帮助人们适应能源的转型,那就是他们更具有凝聚力。在煤矿上,人们习惯于一起工作,对彼此有着依赖性。信任的缺乏是危险的,有时候甚至是致命的。
多年来,鲁尔谷吸收了来自波兰、意大利和土耳其的劳动力。他们已经相处融洽,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交网。蒂施勒说,过去几年,这个只有11.7万人口的小城已经接纳了数千名叙利亚难民。
当然,一个强大的社会结构还不足以挽救一个濒临淘汰的产业。在博特罗普,一些有前景的技术产业和可再生能源将会替代煤炭的地位。
“我认为市长和其他政治家的责任就是把人们的恐惧转变为新的视野、新的动力。”蒂施勒说,“你与他们不是敌人,必须说服他们。你得跟通常不怎么打交道的机构和人一起工作,因为我们是坐在同一条船上的人,我们必须向着同一个方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