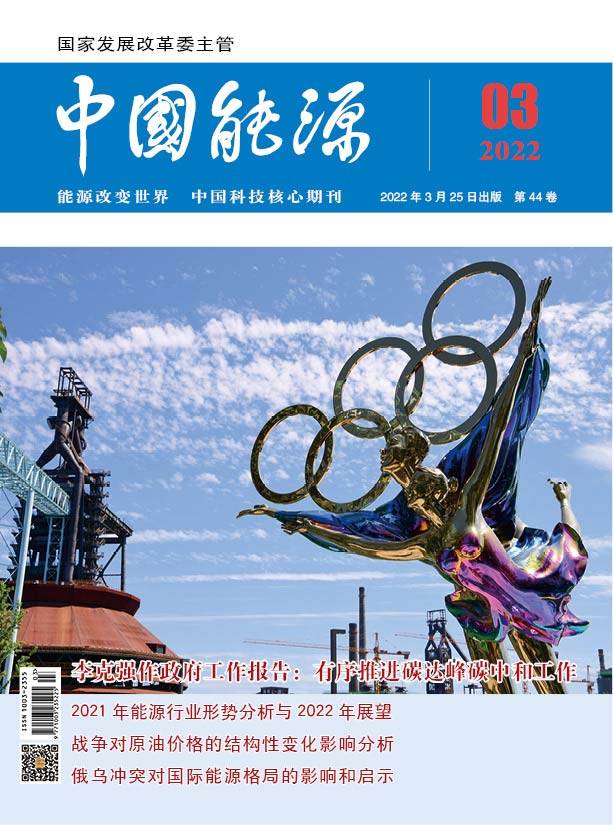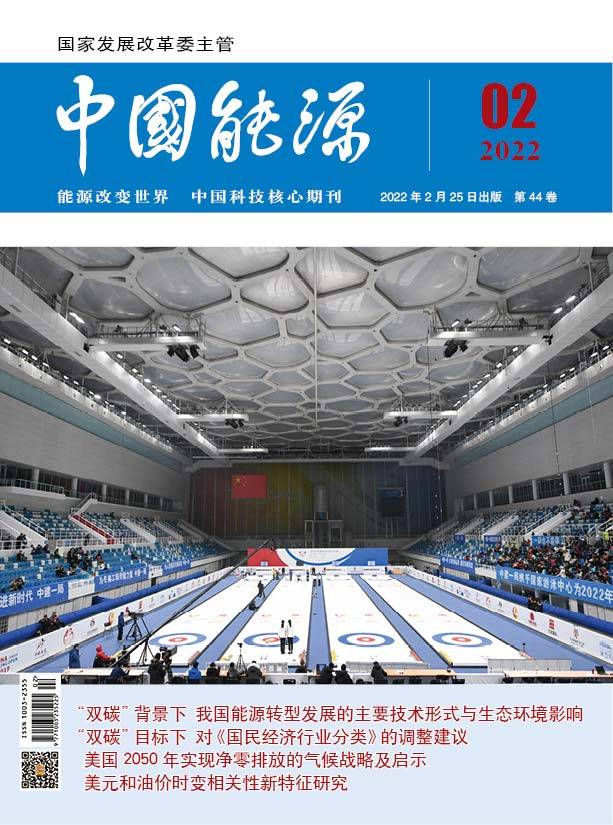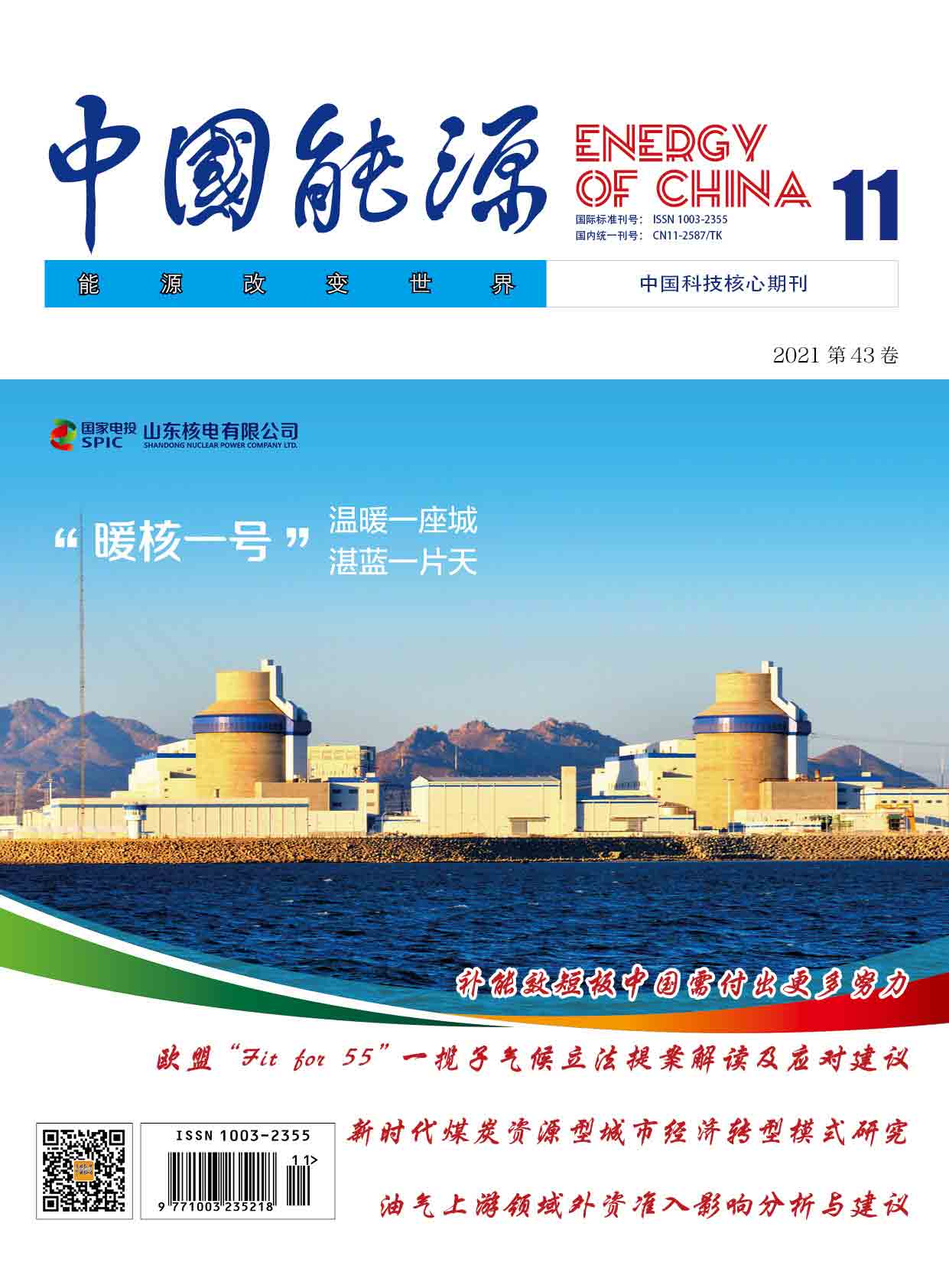当前,随着美国新任特朗普政府立场的倒退和欧盟的后劲不足,以及国际气候秩序和格局的不断演化,全球气候治理正在迈入一个全新的“3.0时代”。
从假说到进程:发达国家主导
从法国科学家傅里叶19世纪初提出关于温室效应的假说,到全球气候变化进入政治和公众的视野,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一般认为,气候变化问题首次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是在1979年,世界气象组织(WMO)在日内瓦召开了第一届世界气候大会,会议号召各国政府“预见和防止可能对人类福利不利的潜在的人为气候变化”,并于1980年和国际科学委员会(ICSU)共同发起世界气候研究项目(WCRP)。1988年,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建立了迄今为止最大也是最有影响力的气候变化研究、评估和咨询机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并陆续发布了五次极具分量的评估报告,着重论证气候变化科学现象的存在,以及人为原因造成气候变化的事实。
上述科学进程直接推动了联合国框架下的政治谈判进程的启动。1990年,联合国大会第45/212号决议批准了气候变化公约的谈判,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政府间谈判委员会(INC/FCCC)在随后两年间进行了5次会议。在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顺利达成并开放签署。时任中国总理应邀出席首脑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该国际公约,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的第一个。
《公约》对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预防、成本效益、可持续发展、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各自能力等一系列重要原则进行阐述,提出了《公约》以及缔约方会议可能通过的任何相关法律文书的最终目标,即“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同时将40个发达国家和欧洲共同体列为了《公约》“附件一”国家,要求其承担起历史责任率先行动,这为今后的全球合作行动提供了“南北两分”的基本框架。这一时期可以称作美欧主导、南北分立的全球气候治理“1.0时代”的开启。
在《公约》正式生效后的次年,即1995年,第一次缔约方会议(COP1)在第1/CP.1号决定中通过了“柏林授权”,同意就《公约》的补充条款及2000年后应该采取何种适当的行动来保护气候进行磋商,以明确在一定期限内发达国家所应限制和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各方最终在1997年的第三次缔约方大会(COP3)上通过了著名的《京都议定书》(KP)。《议定书》按照《公约》的原则和规定对特定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设立了定量限排目标,即在2008年至2012年的第一承诺期内,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应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并提出了履行承诺的排放交易(ETS)、联合履约(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三类灵活机制的初步安排。
1998年5月,中国政府代表签署《议定书》。2002年8月,中国向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交存了中国政府的核准书,并在当年9月于南非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宣布中国已核准《京都议定书》,中国将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履行义务,但并不受强制减排的约束。
当时,美国人口约仅占全球的4%,而二氧化碳排放却占全球的25%以上,是当时最大的排放国。时任克林顿政府曾于1998年签署《议定书》,但2001年新上任的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借口,宣布拒绝批准《议定书》。此后,在美国首次放弃主导权后,欧盟逐步成为了气候谈判进程中的旗手。全球气候治理开始宣告进入新的“2.0时代”。
发展中国家从边缘走向中心
随着经济和排放格局的演变,发展中国家由此迈入共同实施减排行动的阶段。
2007年,《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COP13)启动新的谈判进程“巴厘路线图”,发展中大国开始感觉到要求减排的政治压力。各方对计划在2009年如期达成新的气候协议抱有极大希望,期间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将2007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以鼓励他们“在建立和传播人为引起气候变化问题的知识以及奠定应对气候变化基础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这对当时整个气候谈判进程是一种极大的鼓励和促进。
然而,2009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并未达成共识,欧盟作为东道国领导乏力,《哥本哈根协议》最终流产。但该进程也最终促成各缔约方首次就“全球温升幅度应在2℃以下”达成政治共识。
经历了短暂低潮期后,各方还是逐步重拾多边进程的信心。2015年底召开的巴黎气候大会达成了由197个缔约方通过的《巴黎协定》和一系列相关决议,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近150位国家元首出席该次气候大会,创造了二战以来的最高纪录。
2016年4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代表中国在联合国总部签署《巴黎协定》,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9月3日通过表决批准《巴黎协定》,习近平主席更是在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期间亲自出席了《巴黎协定》批准文书的交存仪式。在中美等大国的大力推动下,《巴黎协定》最终于11月4日满足“双55条件”(即55个缔约方加入且加入的缔约方排放量总计超过全球的55%)正式宣告生效,并进入实质性履约和实施阶段。
截至2017年5月,已有195个《公约》缔约方签署了《巴黎协定》(除了尼加拉瓜、叙利亚),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接近100%;146个缔约方批准或接受了《巴黎协定》,占全球排放83.52%。在此过程中,奥巴马政府与中国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通过两国元首的联合声明、国书递交等形式,传达了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气候外交关系的积极信号。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对全球治理有着更为清晰的方案和主张,有了更为自信、从容的步调,逐步从全球治理体系边缘走进中心。
迎接全球气候治理“3.0时代”
《巴黎协定》的达成,被认为是全球治理中多边主义和双边主义合作共赢的新胜利,很大程度上挽回了当前在联合国改革背景下“参与优先”和“协商一致”等国际理想主义路线的颓势,重新给予此类进程以小步前进的新希望。
然而,《巴黎协定》以鼓励各方最大程度参与、保护各缔约方主权和利益、强调遵约机制中“专家式”的透明、非对抗、非惩罚特性,注重现实起点同时强调不断提高力度为基本特征和精髓的制度安排,虽体现了谈判的妥协艺术和务实主义,但也为其后续落实和实施埋下重重隐患。
尽管《巴黎协定》有了温升2℃/1.5℃和本世纪下半叶碳平衡的目标,以及五年盘点和所谓“棘齿”锁定机制,但对于各缔约方行动的实质内容和力度,没有强制性要求。《巴黎协定》近乎完全“自下而上”的范式强调国家自主、序贯决策,有务实理性的一面,但也将带来“光谱式”的碎片化问题。现有联合国体制下“协商一致”的决策方式,在后期推进国家自主贡献更新、透明度、全球盘点、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关键性机制上缺乏效率、进度缓慢。同时,因为缺乏自上而下的框架,这些机制的设计本身存在一定的困境和障碍,甚至僵局。面对美国现在再次出现的“退约”风波及冗长低效的谈判进程,联合国主渠道的机制需要进一步的反思和改革。
2016年11月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召开的第二十二次缔约方大会(COP22),明确了实施细则谈判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要求最迟不晚于2018年完成《巴黎协定》的操作性安排。气候谈判进程正在走向“技术层面”,但谈判中的主要矛盾并没有解决,众多被《巴黎协定》技巧性掩盖的分歧逐渐又重新浮上水面。比如如何体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区分、是否以减缓为中心以及如何确保发达国家提供有效和充足的支持等。尽管存在波折,但总体而言,全球气候治理正在走上非对抗的、合作共赢的正轨,政府、企业、公民社会等各方力量正在凝聚,共同分享低碳转型效益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当前,世界正密切关注美国特朗普政府是否会兑现其竞选承诺撕毁《巴黎协定》。但不管这一天是否会来临以及何时到来,国际气候秩序和格局演化都已进入一个新时期。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领导力面临更迭和分化,国际社会对治理模式变革以及中国引领未来进程充满期待。中国如何在全球气候治理“3.0时代”更好发挥“气候举旗”的引领作用,提升在国际气候事务中的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需要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更大胆的历史判断。
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当前已经并正在形成一系列新的国际制度和规则,气候资金、技术等方面都会出现创新机制和新兴推动力。培育和形成新的碳要素市场,融入、参与和引导都是借力的方式,也正好嫁接如“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南南合作基金这类展现“中国方案”和“中国主张”的国际开发资本。在进入发展新常态后,中国经济和环境的国情发生了较大改变,也使得国内各界更为积极主动地去思考和推动发展的低碳转型。
一国领导力不是自封的,而是水到渠成的。在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中,中国完全可以为全球和区域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特别是在新兴的绿色发展领域,与世界共同分享低碳转型的经济和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