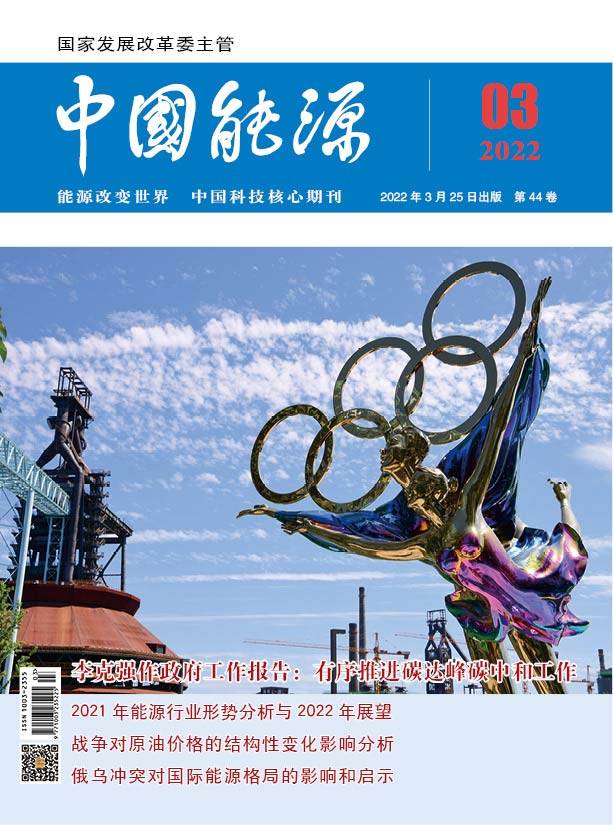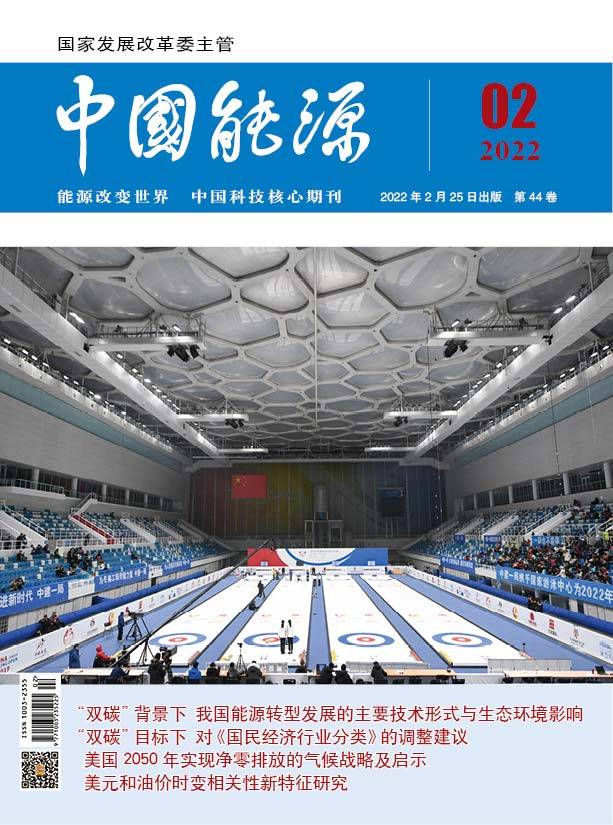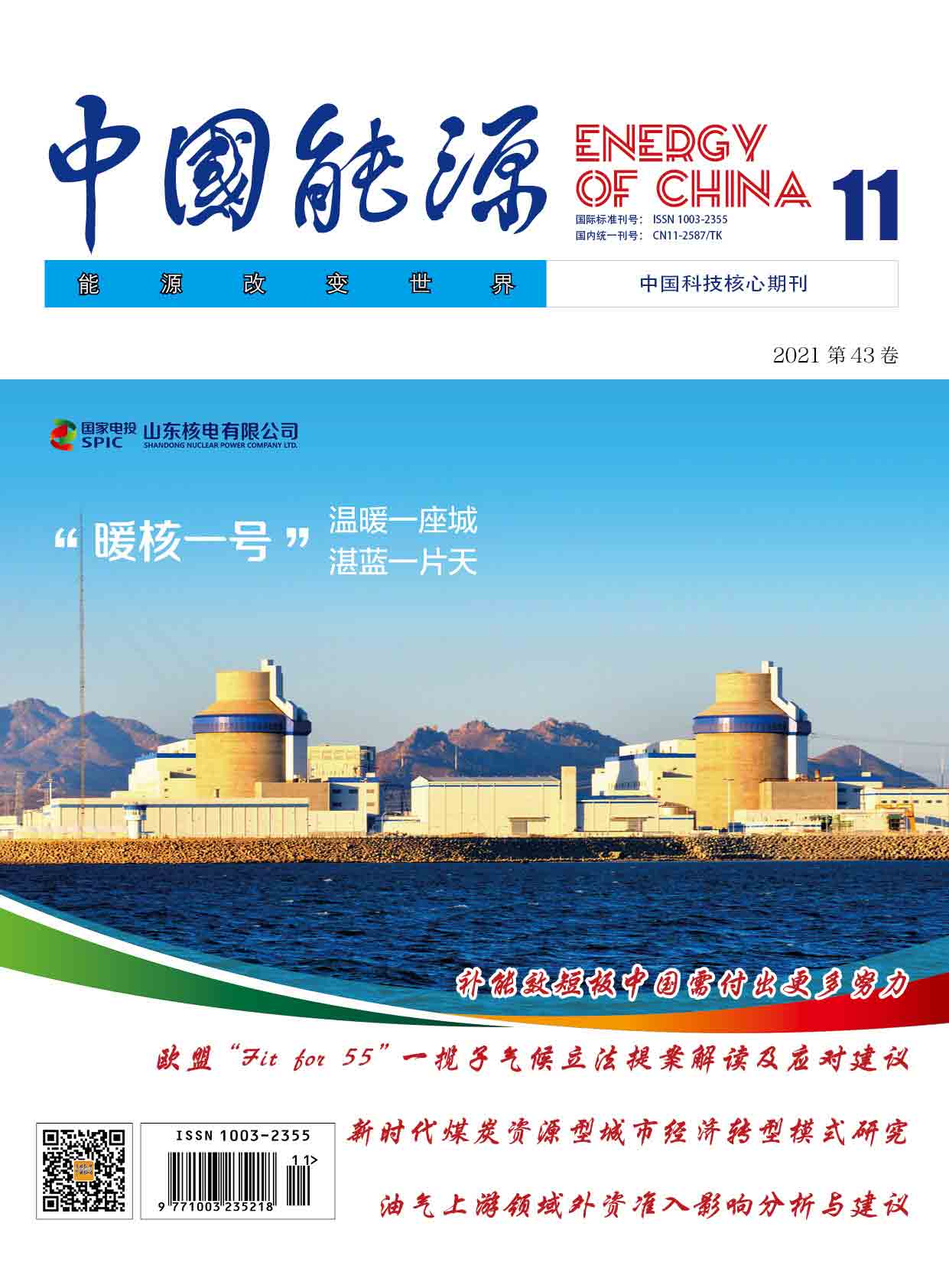中国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把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结构的一个重要的工具。这一举措得到了德班会议与会国家普遍的好评。然而,各国在讨论绿色气候基金的各项运作细节上却各怀心思,分歧甚大。尤其受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美国经济危机的影响,当前气候融资的国际形势扑朔迷离。
首先,300亿快速启动气候资金并非完全是新的、额外的、可预计的、财政的资金,且投向减缓的资金较多,而投向适应领域的资金相对较少。其次,每年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期待来自于公共渠道、发展银行类工具、碳市场和私人部门,但诸多假设条件对于收入评估的影响都非常大,特别是碳价格和国际气候融资比例,资金来源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而且,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主要资金来源方面的主张上存在较大差异。发展中国家出于资金稳定因素,始终主张以公共融资为主,发达国家出于减少公共支出的考量,更倾向于依靠市场力量,普遍认为私人资金和碳市场应成为主要的融资手段。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公共债务普遍恶化,这一分歧也变得更加尖锐。在发达国家的推动下,本次德班会议重点讨论的绿色气候基金运作方案的一个导向,就是私人资本的筹集和利用应成为该基金实现目标的关键。此外,从形式上看,全球气候资金谈判所涉及的范围主要集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之内,但从实质上看,全球气候资金的实质运作重心却又在两个公约框架之外,主要是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纷纷在联合国框架之外利用现有的各种对话平台就气候变化问题展开磋商,以此影响“双轨”谈判进程。显然,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因素将推动气候融资谈判机制向“多轨”发展。
在复杂的国际气候融资形势下,我国仍是国际气候资金筹集和运用得最好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当前,我国利用国际气候资金的主要来源包括CDM收入、多边开发机构的资金支持和国外私人部门的投资。此外,我国政府推出了大量促进节能减排、刺激绿色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相应也带动了国内气候资金的投入。但是,我们对气候资金的管理、筹措与运用仍存在大量问题。
从管理上看,我们不仅缺少气候融资战略,也没有统一的气候融资管理体系,主要表现在气候资金来源分散且尚未单独核算、审批与管理部门多头并行。尤其是国际气候融资,因涉及外资的进入及监测监管,以及国际气候谈判中的气候融资的核算,这个问题更显严重。从资金来源上看,CDM机制国际政策层面的中国前景不很乐观,以项目为基础的CDM很可能将仅限于在最不发达国家开展。多边开发机构的资金规模直接决定于资金机制的总体出资规模,由于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由美国所主导,亚洲开发银行由日本和美国所主导,要吸引更多的多边机构资金,需要进一步加强多边及双边的融资谈判实力。当前国内气候融资主要以财政性工具为主,且支持力度有待加强;金融性工具尚未发挥出应有作用。从资金运用上看,以投资于节能减排项目、可再生能源项目等缓解领域的居多,而投资于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地和水资源保护等适应领域的资金相对较少。
在应对气候变化及绿色经济转型的全球背景下,清晰把握国内外气候融资的规模、流向以及治理情况不仅是我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需要,也是我国推进绿色经济转型,高速集聚绿色竞争力的关键。因此,我国应立足自我,保持国际气候融资的优势,并大力发挥国内气候融资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第一,设计良好的气候融资监管框架。明确气候融资的归口管理部门,出台系列气候融资政策,制定相关的监管和激励措施,引导国内气候融资流向,并从减缓和适应两方面,充分考虑其主要的资金来源,积极创新融资渠道。加强气候资金的核算与监管,关注资金安全。
第二,充分利用国际气候资金。中国面对经济高速增长与碳排放最大国的尖锐矛盾,气候变化领域的发展合作可以成为我国吸引更多官方发展援助的有利条件。应提高多边与双边谈判能力,争取双边渠道的官方资金、国际和区域政策银行的优惠贷款。
第三,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的投入,优先关注绿色行业。运用税收优惠、贴息、担保、奖励、风险投资等方式支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的建设,带动其他资金和社会资金参与。
第四,审慎设计碳交易机制,大力发挥碳交易市场的金融功能。碳交易政策效用能否得到有效发挥,在乎于体系设计是否精心合理,否则将可能给未来的监管带来巨大的成本,造成社会福利净损失。
第五,充分利用金融服务和投资部门的气候资金。健全绿色信贷机制,引导商业银行资金向绿色行业倾斜。增强政策性银行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投入或考虑设立政策性绿色银行。充分利用上市金融机构、主权财富基金、保险基金等长期投资者控制而短期内不需要变现的资产。发挥资本市场在气候融资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开发其他金融工具和融资手段,如绿色融资租赁、绿色信托、绿色债券、绿色融资担保等。